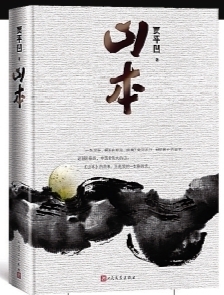
◎唐山
“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,而是从天、地、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,挖掘人与人、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,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。”对于刚出版的、个人第16部长篇小说《山本》,贾平凹如是说。
《山本》聚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南小镇——涡镇,并以此为切片,展现出整个秦岭史内部的生长逻辑——冰冷而坚硬的现实,顽强的生命意志,充满韧性的道德情怀,朴野却偏执的性格……然而,历经搏斗、向往、背叛、血腥、忠诚之后,没人真正逃出命运的安排,他们终归沉寂——就像秦岭一样,默默地成为下一代人的布景。
与贾平凹的每部长篇小说一样,《山本》加入了许多创新,但它与贾平凹的每次创新一样,并未彻底背叛那个曾经的贾平凹。
《山本》是又一本“非常贾平凹”的小说,感动于作家的坚持,却又多少有些遗憾。
没有英雄了,世道就好了
整体上说,《山本》依然延续着“寻根文学”的脉络。该派以1985年韩少功《文学的“根”》中“文学有根,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”“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,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”为始,阿城、贾平凹是其中代表作家,以后逐步发展为书写民族史的巨流。
严格意义上的“寻根文学”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终结,贾平凹后期写作也带上了新写实小说的色彩,但其作品中的“寻根”色彩始终留存。读《山本》,很容易想起《高老庄》《古路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等,同样是在用写史的笔法来写小说,同样是在用一个侧面来展现整个民族史。
《山本》以寓言为始:陆菊人的母亲去世,因家贫无钱买棺,父亲只好将她许给涡镇开棺材铺的杨家当童养媳,而陆意外得知家中的三分地“胭脂地”暗通龙脉,便要父亲把这块地给她当嫁妆。出乎陆菊人意料,因同情井家劫难,杨家允许死无葬身之地的井掌柜埋在“胭脂地”,井家二子井宗秀果然转运,当上涡镇首富,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成为一方豪强。
几乎所有英雄传奇都有这样半真半假的开始,而水在其中常充当重要作用。比如罗马的创始人罗慕洛斯出生不久便被置于篮中顺水漂流,摩西、玄奘、岳飞均享受过同等待遇。在早期评书中,关公就擒前,特意将青龙偃月刀扔入水中,而孙悟空则从水中捞出了一根棒子。揭幕于水,闭幕于水,这是东西方共通的英雄叙事潜意识。
《山本》中的涡镇也有条河,却是两股水构成的漩涡,它永远在吞噬,绝无任何吐露。它像黑洞一样陪伴着涡镇人,仿佛是对人间一切挣扎的莫大嘲讽。
围绕着涡镇这方舞台,人们纷纷登场:一心想建功立业却最终沉迷于动植物学的麻县长、豪横一生却被手下割了生殖器的土匪五雷、胆大心细却死在叛徒之手的井宗丞、使井宗秀成为英雄却又看着他沉入张狂的陆菊人……
《山本》长达45万字,却高度浓缩,故事含量惊人,如采用传统写法,至少需三四百万字才能讲清。如此纷繁的生命故事,概括起来,无非是瞎子陈医生的那句话:没有英雄了,世道就好了。
自以为是龙,其实是鳖
然而,生在乱世,当英雄是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井宗秀从没设计过人生,仅仅是为了高人一等,被逼上了当英雄的不归路。他足够精明,辅以陆菊人的鞭策。二人在似是而非的爱情中,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
事实上,陆菊人早就洞悉了命运:井宗秀只是历史的一个结果,时代将他涂满亦正亦邪的色彩——他利用土匪五雷霸占他人财产,使自己成为涡镇首富;利用小姨子搞“连环计”,将五雷置于死地;又利用麻县长驱逐土匪,使自己能独霸一方……
井宗秀始终在几方势力间借用。当他的哥哥井宗丞因奸细三猫而死,他用最江湖的方式泄愤。在英雄幻觉下,井宗秀渐渐丧失自我,他崛起的代价是无数小人物的死,乃至涡镇的毁灭。
艰辛与不堪,拼成了《山本》。这段历史深深地沉入在一代人的基因中,所以在面对未来时,我们才会如此惶惑。
历史是利益博弈的产物,而非道德合理性的产物。越了解历史,我们便越会被它的暗面震惊,只靠历史,是无法引导人们走向明天的。
那么,该如何重建道德想象力?如何突破恶与恶循环的死结?
在后记中,贾平凹写道:“《山本》里没有包装,也没有面具,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,不管是非功过,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、慌张、恐惧、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。”
麻县长曾给井宗秀算命,让他报三个动物,井报了龙、狐和鳖。
麻县长的答案是:第一个动物代表对自己的评价,第二个动物代表别人的评价,第三个动物才表明根本。
井宗秀想成为龙,但在乱世之中,只有忍耐、静寂、大智若愚,才能活下去。
为什么要书写民族史
这些年来,类似的民族史写作不罕见,如迟子建的《群山之巅》、格非的《望春风》、葛亮的《北鸢》等。相比之下,贾平凹的写作有独到之处,即融入了新现实小说的笔法,即:放弃传统的“三一律”式、过度戏剧化结构,平静叙述生活本身,通过散点透视,展现生活的本来状态。
早在《废都》后记中,贾平凹便写道:“中国的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,读它的时候,哪时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?恍惚如所经历,如在梦境。好的文章,囫囵囵是一脉山,山不需要雕琢……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,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。”
《废都》后很长一段时期,贾平凹的小说并没有脱离主角与故事情节,但到《高老庄》时,已转向描写群体,而推动情节的力量已是偶然,而非精心的设计。
到2016年推出长篇小说《极花》时,贾平凹称:“我开始写了,其实不是我在写,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。”
成熟的创作者最终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:在过于强大的写作技术压迫下,难以找到自我,当提笔便是套路、便是“不得不如此”时,刻意放弃写作技术乃至反技术,也是一种自我突破。
将小说转为“唠叨”,优点是抹平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区别。毕竟现实是多元的,未必存在一个发生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尾的脉络。在生活的舞台中,人人都是自己内心的主角。事实是,刻意塑造出来的主角与刻意塑造出来的情节,仅能传达一种声音、一种经验,在震撼读者的同时,也在愚弄读者。可问题是,小说不是现实,它需要观众,这决定了:小说永远无法抵达所谓的生活真实,只能止步于艺术真实。如何将读者绑架到同一个剧场中、让他们产生共同的时间呢?
贾平凹选择了书写民族史,这很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。
小说不能只比下笔熟练
然而,站在书写民族史的角度,《山本》有值得商榷处。
其一,部分语言、材料太新颖,没有史的距离感。
比如麻县长给井宗秀算命,让他列举三种动物,本是常见的、游戏用的心理测验题,让“满腹诗书”的麻县长突然变身为无聊网友,让人有些难以接受。小说怕穿帮,类似亦今亦古的穿帮甚至已成贾平凹的写作特色。在《山本》中,闲汉们多处语言互撩中亦显出当代腔。
其二,有些意象在既往小说中已反复出现。
比如割生殖器,在《秦腔》《老生》《油月亮》等作品中均有,在《山本》中,不仅五雷被割,井宗丞也差点自割(因为没找到刀,得以幸存,他甚至还一度想到火烧法)。
再刺激的情节,如此重复,便难称妙笔。
其三,无意义的魔幻。
贾平凹的小说中常有魔幻色彩,但分量不多,且与他擅长的细节描写不协调。贾平凹炼字准确、传神,善于营造真实感。可在《山本》中,不论是野蜂,还是漩涡,乃至动辄飘下的皂荚,都带着强烈的炫耀气息,似乎这样就能给小说注入国际色彩。
其四,带有非黑即白的气息。
淡化了主角与故事情节,可人人都带上主角腔,所有细节都显戏剧化,这就很容易给读者以重复之感。“生活流”复归了现实的琐碎、偶然和平静,可代价是缺乏持久的故事动力,只能靠残酷、血腥、惊悚之类来吸睛。在《山本》中,土匪、枪战、撕票、变态、虐待等一一得到展示,可类似写作太多,使这些场面均难构成刺激。也许用惊人的恶能衬托出生命韧性,只是恶不再“惊人”时,生命韧性也就变成了“不过如此”。
值得反省的是:书写民族史这一条路是否已走到尽头?当它呈现为程式化、远离现实、批判乏力时,该如何开新?毕竟小说中没有规定动作,不能只比下笔熟练。
作家们钟爱书写民族史,常常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现代性,他们对人的无限膨胀感到恐惧,只好虚拟一个“天地之道”来呼唤敬畏。可在放大“天地之道”神秘感的同时,不能把人摆在从属地位,片面夸张命运、历史、永恒之类的魔力,这不仅阉割了文学中最具活力的部分,且很容易走向历史循环论式的反智,最终被绝望与邪气所笼罩。
在《山本》中,当涡镇毁灭时,活下来的只有习惯于隐忍的小人物们。“天地之道”终归于虚无,那么,我们究竟该敬畏什么?究竟该何去何从?
如果答案只是“从来如此”的话,又何必写成小说?



 ×
×